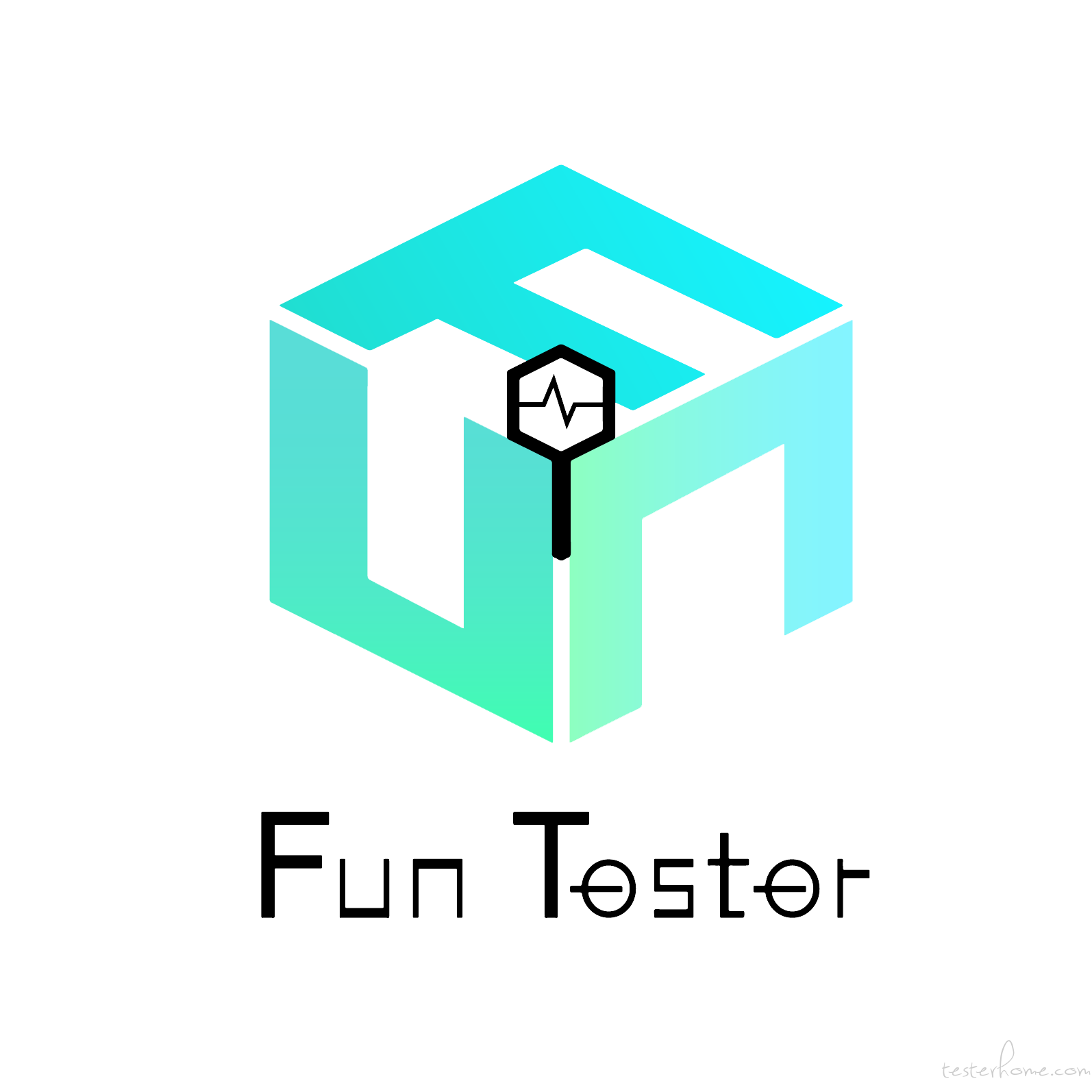最初的时候,巨磨场并不排斥异样的步伐。磨盘转速稳定,磨道宽阔,蹄印之间还留着选择的余地。有人走得慢一点,有人走得直一点,并不会立刻显得突兀。马站在高阈廊道上,看的是整体磨相,语气温和而克制:每条路都有它的节奏。那时,这句话更像经验,而不是裁断。牛在后槽踏磨,稳扎稳打,把硬节一块一块踩实;骡在边磨区被抽去顶硬节,跑得快,也还会抬头看一眼前方的坡度,判断自己是不是偏了方向。
变化并不是从禁止开始的,而是从 “不合时宜” 开始的。磨令依旧模糊,磨契却在细节处悄然生效。有人坚持按原来的节奏踏磨,被提醒不够协同;有人把磨役做得过于扎实,被评价不够灵活。马在廊道上抬磨,说这是磨力分配的问题,不是对错。回声在廊道里扩散,很快盖过了具体细节。牛有一次慢下来,想把一段硬节彻底踩稳,却发现后面的磨潮迅速顶上来,逼得他不得不重新加快步伐。骡跑得最急,却在一次次被抽磨中意识到,方向从来不是他能决定的。
逆着走,并不会立刻被拉走。它更像是一种被悄悄标记的状态。磨痕册里,多了一些看不见的符号,记录的不是错误,而是态度。那些不愿绕磨、不擅抬磨的兽,被默默归为 “需要观察”。牛曾经拒绝过一次明显不合理的补磨,语气依旧温和,却在之后的踏序里,被连续安排到更硬的节段。他没有争辩,只是比以前更沉默。骡试着问过一次为什么,得到的回答很简单:踏久了就会懂。
磨道开始收紧。不是整体变窄,而是直线越来越少,弯道越来越多。弯道本身并不难,难的是谁更愿意弯。马在高处指路,说这是为了提高整体磨效。绕得顺的,很快被看见;走得直的,被认为不懂变通。奉承逐渐取代解释,回声比事实更安全。骡学会在关键节点低头,把疑问咽回去;牛学会在被压磨时先点头,再继续撑磨。内卷并不需要竞争口号,只需要让所有人都不敢慢下来。
真正的压榨,也不再表现为明显的强迫。它藏在比较里,藏在 “别人都能走” 的暗示里。骡发现,只要他稍微停顿,就会有人更快地补上来;只要他多跑一段,原本属于别人的负担,就会顺理成章落到他身上。牛发现,只要他还愿意扛,踏序就永远不会轮到他调整。磨场里没有人明说,但所有兽都心里有数:不顶上去,就会被挤下去。
逆着走的代价开始显现,却依旧不显眼。先是被换离主磨道,再被安排到边磨区,最后落入暗磨井。没有宣告,也没有冲突,只是磨令不再点名。磨盘照常转动,磨影却慢慢淡去。有人注意到空出的磨位,却很快被新的步伐填满。奉承在此时显得格外重要,它能证明你还在队伍里,还在节奏中。
马依旧站在高阈廊道,说风向很好,说留下来的都是适应者。他很少提起那些消失的蹄印,只强调磨道的顺畅。牛还在踏磨,只是再也不提自己的节奏;骡依然能跑,却不再抬头看坡。他们都学会了一件事:逆着走,并不会立刻倒下,但一定会慢慢被挪走。
某个踏磨日结束时,磨道上少了几道熟悉的印记。没有人询问去向,磨痕册也没有更新说明。磨场显得比以往更有序,磨盘转得更顺,蹄印排列得整齐划一。逆着走的,从来不是被击倒的,而是被悄无声息地排除在节奏之外。巨磨场并不惩罚逆者,它只是让他们,再也找不到继续走下去的位置。